
中金认为,二季度特步主品牌全渠道流水同增10%,主要由线上拉动、线上流水同增25%。此外,公司库存周转更加健康,零售折扣、库销比环比改善。该行指出配资优秀炒股配资门户,新品牌索康尼、迈乐表现出色,预计盖世威、帕拉丁于三季度内完成剥离。若成功剥离后上市公司层面有望大幅减亏,贡献利润弹性。

一条北京中轴线,纵贯南北,连接古今,被称为“北京城的脊梁和灵魂”。作为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识,北京中轴线南起永定门,北至钟鼓楼,全长7.8公里,是当今世界最长的城市轴线。不久前,“北京中轴线”申遗成功,这条跨越700余年的“线”再次惊艳世界。多少年来,无数作家曾在这里留下足迹,写下作品,这条“线”在他们笔下经山历海,日久弥新。循着他们的文字,走过钟鼓楼、万宁桥、景山、故宫、天安门、太庙、社稷坛……这条城市轴线在人们眼前日渐鲜活,伟大的中华文明在文学的书写中熠熠生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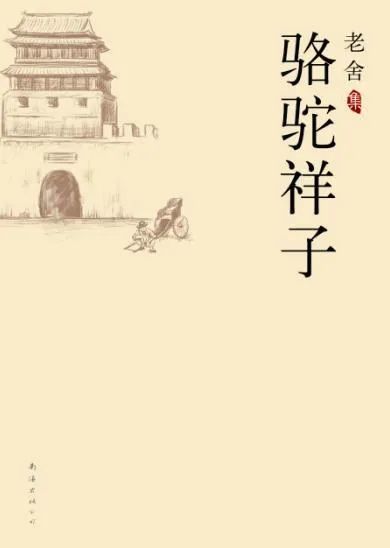
《骆驼祥子》,老舍著,南海出版公司,2010年3月
《骆驼祥子》
老舍
风把灰云吹裂开一块,露出月光,二人已来到街的北头。御河的水久已冻好,静静的,灰亮的,坦平的,坚固的,托着那禁城的城墙。禁城内一点声响也没有,那玲珑的角楼,金碧的牌坊,丹朱的城门,景山上的亭阁,都静悄悄的好似听着一些很难再听到的声音。小风吹过,似一种悲叹,轻轻的在楼台殿阁之间穿过,像要道出一点历史的消息。虎妞往西走,祥子跟到了金鳌玉蝀。桥上几乎没有了行人,微明的月光冷寂的照着桥左右的两大幅冰场,远处亭阁暗淡的带着些黑影,静静的似冻在湖上,只有顶上的黄瓦闪着点儿微光。树木微动,月色更显得微茫;白塔却高耸到云间,傻白傻白的把一切都带得冷寂萧索,整个的三海在人工的雕琢中显出北地的荒寒。

《李健吾文集》,李健吾著,北岳文艺出版社, 2016年5月
《北平》
李健吾
北平的城像一个“凸”字,也像一辆铁甲车。平剧《梅龙镇》里面,明朝的正德皇帝用一个比喻说到他的住所,大意是:大圈圈套着一个小圈圈,小圈圈又套着一个小圈圈。所谓大圈圈,就是北平的外城,凸字的下半截;所谓小圈圈,就是北平的内城,凸字的上半截。城虽说分做内外,并不是圈圈,也并没有谁圈着谁。只有那个小而又小的圈圈,的确套在内城的中心,通常另有一个尊贵的名称,叫做紫禁城。
紫禁城又有一大一小:小的是禁城,里面住着一个皇帝,现在没有了皇帝,通常叫做故宫,大的是皇城,或者黄城,因为墙是土红色,仿佛庙宇的墙垣,其实颜色不是黄的,也不是紫的。
北平的美倒也不在这些里里外外的城堞。城楼大半做了鸽子窝,砖缝布满了荆棘,一个过去的世纪静静摆在你的眼前。
要想领略北平的美,最好是坐飞机来一个鸟瞰。否则站在禁城的午门上面,瞭望一下四野也就成了。一片绿意,我这个“野”字用的并不过分。房子隐隐呈现在枝叶下面,街道像似一条一条细流,粼粼散开,匀整而不单调,映着红墙碧瓦,仿佛一幅古色古香的锦缎金绿的底子。街道做成灰色的方格,有红花碧梗点缀。

《人间有味》,汪曾祺著,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年4月
《午门忆旧》
汪曾祺
午门是紫禁城总体建筑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。这是故宫的正门,是真正的“宫门”。进了天安门、端门,这只是宫廷的“前奏”,进了午门,才算是进了宫。有午门,没有午门,是不大一样的。没有午门,进天安门、端门,直接看到三大殿,就太敞了,好像一件衣裳没有领子。有午门当中一隔,后面是什么,都瞧不见,这才显得宫里神秘庄严,深不可测。
午门的建筑是很特别的。下面是一个凹形的城台。城台上正面是一座九间重檐庑殿顶的城楼;左右有重檐的方亭四座。城楼和这四座正方的亭子之间,有廊庑相连属,稳重而不笨拙,玲珑而不纤巧,极有气派,俗称为“五凤楼”。

《秦牧散文》,秦牧著, 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年5月
《社稷坛抒情》
秦牧
北京有座美丽的中山公园,公园里有个用五色土砌成的社稷坛。
社稷坛是北京九坛之一,它和坐落在南城的天坛遥遥相对。古代的帝王们,在天坛祭天,在社稷坛祭地。祭天为了要求风调雨顺,祭地为了要求土地肥沃,祭天祭地的终极目的只有一个:就是五谷丰登,可以“聚敛贡城阙”。五谷是从地里长出来的,因此,人们臆想的稷神(五谷)就和社神(土地)同在一个坛里受膜拜了。
穿过古柏参天,处处都是花圃的园林,来到这个社稷坛前,突然有一种寥廓空旷的感觉。在庄严的宫殿建筑之前,有这么一个四方的土坛,屹立在地面,它东面是青土,南面是红土,西面是白土,北面是黑土,中间嵌着一大块圆形的黄土。这图案使人沉思,使人怀古。遥想当年帝王们穿着衮服,戴着冕旒,在礼乐声中祭地的情景,你仿佛看到他们在庄严中流露出来的对于“天命”畏惧的眼色,你仿佛看到许多人慑服在大自然脚下的神情。

《王蒙散文》,王蒙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8年1月
《故宫的上元灯火》
王蒙
后来我又多次去过故宫,对它有了更好的了解,但儿时对故宫的印象,时而浮现脑海。2019年上元佳节晚上,我进入了故宫,我登上了紫禁城,我第一次感觉到了故宫的亲和、美丽与可爱。我看到了故宫建筑上高挂的大红灯笼,灯笼照亮了夜空,照红了照活了照喜兴了亭台楼阁,我也看到了变幻动态的射灯把大殿屋顶照得辉煌壮丽,把角楼轮廓照得美轮美奂,把城市的夜景与故宫的历史用组组灯光编织起来,成为一体,与高挂天空的正月十五的明月对映着,互动着。我与幸运的万千市民、男女老少一起,聚集着、簇拥着、快乐着、呼唤着,登上故宫城墙,在工作人员的关照引领下,走过一段又一段起伏的石头道路与木板台阶,走过殿堂,经过书画与器皿的展示,看到了映照在大殿屋顶的《清明上河图》投影。我感到惊奇,不可思议,怎么出现了另一个故宫?是新的、贴近的、人民的、热闹的、红火的与吉祥喜乐的故宫,是庙会一样、广场一样、自家一样、社区一样的故宫。这是故宫吗?抑或是北京街市嘉年华?大联欢?可它明明还是那么巍峨雄壮,还是那么高端大气,还是充盈着尊严感。你看到了故宫的全貌,也看到了天安门、中山公园、文化宫、交民巷、前门大街……北京的中心区域,尽收眼底。
人们说,这是故宫建设600年来首度夜间亮起来热烈起来;是故宫博物院建院90多年来第一次在夜晚开放。灯光亮过了星月,鼓乐结合了笑语,天黑后让大家玩了起来乐了起来。如今的我,完全没有了十几岁时老师领着我们走在这里时的恐惧,有的只是躬逢其盛的欢喜。
《最美中轴线》
高洪波
北京中轴线是北京市正在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项目,有十几个遗产点,具体说来是:永定门、先农坛、天坛、正阳门及箭楼、毛主席纪念堂、人民英雄纪念碑、天安门广场、天安门、社稷坛、太庙、故宫、景山、万宁桥、鼓楼及钟楼。这个中轴线总长7.8公里,占地面积600公顷。
我在北京已经居住多年,北京中轴线的概念,我认为更主要的是涉及文化自信的政治概念,也是涉及人文风景的地标概念。
北京中轴线从永定门说起,到鼓楼结束,对于我而言,拥有太多的遐思和记忆。永定门有一个老的火车站,那是在遥远的1969年2月,我们一批北京的中学生就是在永定门火车站登上了闷罐列车,穿着还没有帽徽领章的新军装,向遥远的云南进发。七天七夜漫长的行旅,一批穿上新军装的中学生在祖国大地穿行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觉?什么样的体会?不用我多说,所以永定门火车站是我刻骨铭心、终生难忘的记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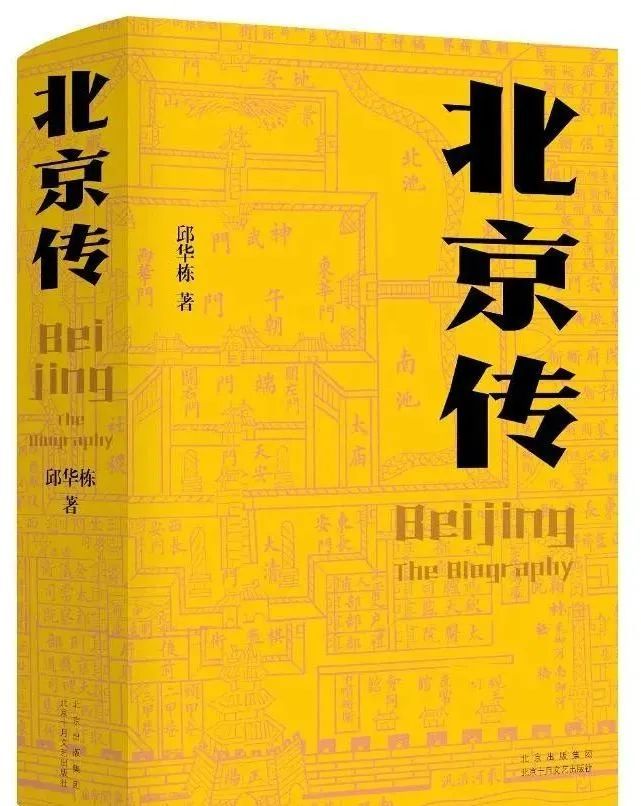
《北京传》,邱华栋著,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0年
《北京传》
邱华栋
明皇宫紫禁城的周长六里,城墙是重五十斤的大砖砌成的,高达十米,南北长九百六十米,是一个长方形。城外还有一条筒子河,宽达五十米。从午门向北,就是玄武门,东为东华门,西为西华门,各门都有城门楼子,宫城的四角还有角楼,现如今这角楼依旧是故宫的一大景色。其中,以故宫东北角的角楼与筒子河形成的风景区最漂亮。
进入午门向北,就是巨大的宫廷合院,东是会极门,西是归极门,院子中间就是金水桥。穿过合院,正北是皇极门,这是外朝三大殿的正门。左边叫弘正门,右边叫宣治门,而皇极门的东边是文华殿,西边是武英殿,遥遥相对十分对称,是明代皇帝和文人学士讨论文化问题,和武将将军讨论军机大事的地方。
明代的皇宫三大殿,分别是皇极殿、中极殿和建极殿。
皇极殿又叫金銮宝殿,是当时紫禁城内最高大巍峨、庄严肃穆的殿宇,大殿建在须弥座台基之上,殿前的广场有三万多平方米,大殿面阔九间,六十四米宽,大殿屋顶高二十七米左右,气势非凡。在殿内安放皇帝的宝座,四周围绕着巨大的蟠龙柱,是明朝皇帝登极、朝会、大典、发皇榜和颁发重要诏令的地方。中极殿是皇帝在去皇极殿之前休息的场所,而建极殿则是皇帝宴请王公贵族和大臣的地方。
皇极殿一开始叫作奉天殿,中极殿一开始叫作华盖殿,建极殿一开始叫作谨身殿。为什么改了名字?是因为一场大火。
公元1421年四月初八,也就是永乐十九年,这几座宫殿才建成九十多天,忽然,宫中建筑遭到雷击,失火燃烧起来,大火熊熊,一下子把刚建好的三大殿奉天殿、华盖殿、谨身殿全部烧毁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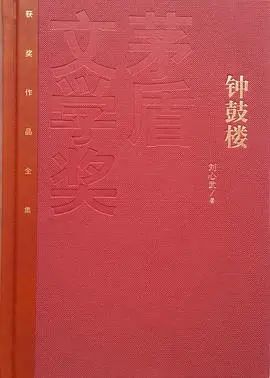
《钟鼓楼》,刘心武著,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5年1月
《钟鼓楼》
刘心武
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,一束蛋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。
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。北城的所所房屋渐渐显出了它们的轮廓。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,也渐渐显出了它们那雄伟的轮廓。
鼓楼——又称谯楼——上,传来交更的阵阵鼓声,打破了这夜空的寂寥。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。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。同它的前一夜一样,并且同它的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。
天光渐渐放亮。
随着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,沉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。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,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,在微风中摆动着;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,包着铁皮的车轱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;卖茶汤、豆腐脑、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,就是修理匠们,也开始沿着街巷吆喝:“箍桶来!”“收拾锡拉家伙!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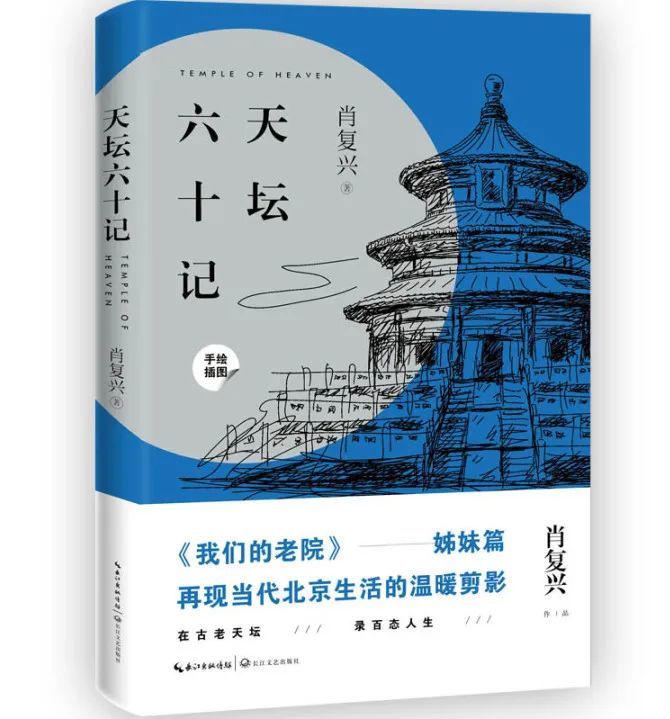
《天坛十六记》,肖复兴著,长江文艺出版社,2021年1月
《天坛十六记》
肖复兴
天坛的入门,以前没有东门、北门和南门。天坛的正门是西门,名叫祈谷门。当年皇上来天坛祭天的时候,走的就是这道门。门是地道的皇家坛庙的老门,三间开阔,红墙红门,拱券式,歇山顶,黑琉璃瓦铺设,在天坛独一份,一直延续至今。
进入内垣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二道墙门,叫作西天门,门前是一条宽阔的大道。以前,道两旁有很多方形的石座,是当年插旗杆的东西,如今,一些残存的石座移到斋宫南门之外。在原来放石座的地方,摆放着花盆,秋天的时候,盛开着鲜艳的三角梅或串红和孔雀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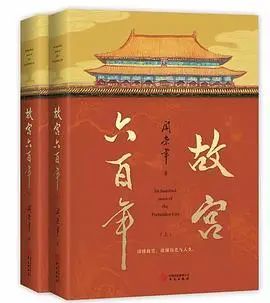
《故宫六百年》,祝勇著, 人民文学出版社,2020年5月
《故宫六百年》
祝勇
首先,因为我们对故宫的认识是从空间开始的,我们会站在某一个位置上,看那浩瀚的宫殿,携带着它所有的往事,在我们面前一层层地展开。本书的讲述,也像所有走进故宫(紫禁城)的人一样,开始于午门,然后,越过一道道门,从一个空间走向另一个空间。全书共十九章,除了前两章综述了它的肇建过程和整体结构以外,在其余的十七章里,我把故宫(紫禁城)分割成许多个空间,然后,带着读者,依次领略这座宏伟宫殿。
其次,也是更主要的原因,在于中国人的时间意识,最早是通过空间获得的。在周代,中国人通过立表测影以知东南西北,进而划分出四季:正午日影最长的为冬至日,最短的为夏至日,那么在这最长最短之间的中间值的两个日子就是春分与秋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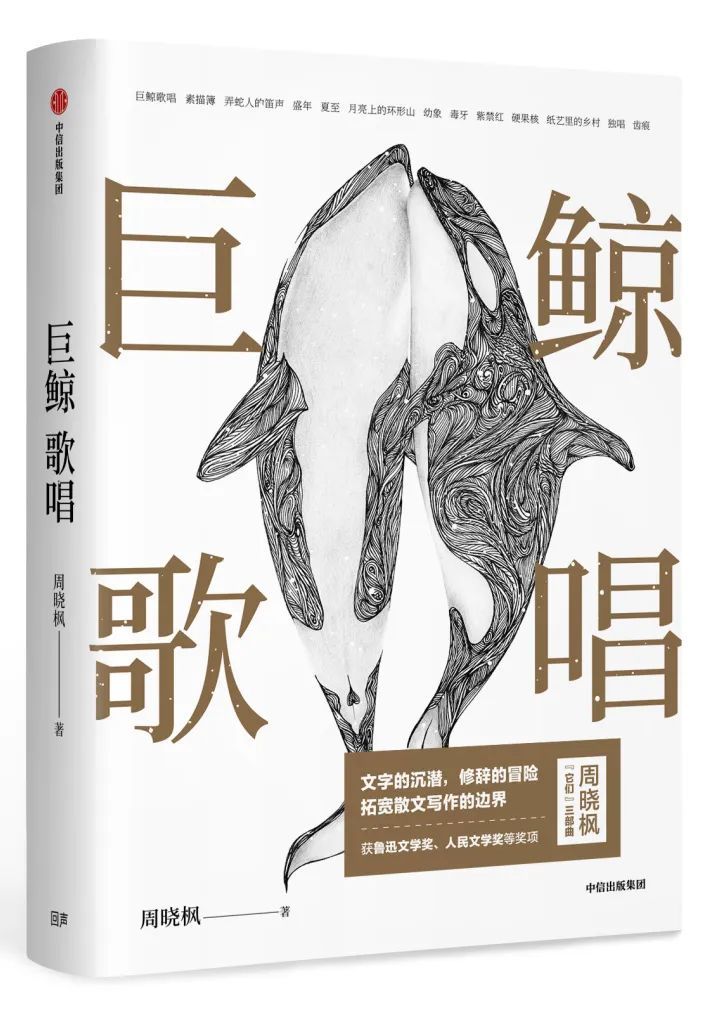
《巨鲸歌唱》,周晓枫著,中信出版社,2019年7月
《紫禁红》(节选)
周晓枫
参观过许多塔,我记得砌面上的琉璃雕饰如何反射着残阳,佛像法相庄严、风雨不侵,或者木质的角檐如何被蛀蚀,留下让风穿过的孔隙。登塔,躬身绕着旋转的梯子,直至顶部──仿佛进入一只锥螺的壳,感觉自己是受到攻击而回缩的肉体。透过高处的窄窗眺望,四野无极。
我们难以追及古代工匠的智慧,他们建造宫殿不用半根铆钉,到处充满玄奥的榫接,为了翻修而进行的拆除使建筑师也陷入尴尬,因为不能将拆散的它们复原。而千百年的一座塔,亦如定海神针般不移,捍固在历史的沙床。置身塔顶,我得以在某种保护里,被古老的辉煌之光映照,感受高瞻远瞩的文明。
无论是男童哪吒还是女妖白蛇,这些挑衅中的角色必须用塔来镇压:塔的内部更接近牢笼,让受惩者不能翻转身体;塔的外部更接近纪念碑,具有从天而降不可撼动的正义感。我有个偏见:相较于其他,塔更像有腹腔或深藏心脏的建筑。事实如此,塔里常藏着经卷、舍利以及许多不可轻易触碰之物,包括它自身的阴影。
许多时候,北海的白塔作为背景存在,它是照相机中的远方。我最为珍贵的几张旧照是在北海拍的,白塔总是在中景以外,显得有点矮小。九岁的我坐在船尾,从父亲的肩膀后面露出头来,脸上挂着小鬼般的诡黠神情。由于拍摄的瞬间船身突然晃动,照片的水平线倾斜,白塔恰巧出现在我额角的位置,既像一个镇妖之宝,又像从我头上长出一根怪异的角。
我记得拍照片的那个四月,春光如织,空气中仿佛有能被指头拨弄的金丝弦。我记得书包里提前准备的野餐:从糖水罐头里捞出光滑的黄桃;午餐肉带着不健康的浅粉色;面包上结痂似的硬皮。我记得在岸上采摘的蒲公英,风把它们蓬松的球冠吹散,葬在粼粼碧波之中。依照常识课要求,我收集过多种植物标本,把花叶压在字典里,它们枯死过程中会顺便弄脏几个词条。但蒲公英虚幻主义者的头部,导致它们难以制作成标本。
我唱过那首著名的歌儿: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。水中倒映着美丽的白塔,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。小船儿轻轻,飘荡在水中,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。”恍惚之中,我并未发觉,正午的白塔,作为日晷上的秘密指针在移动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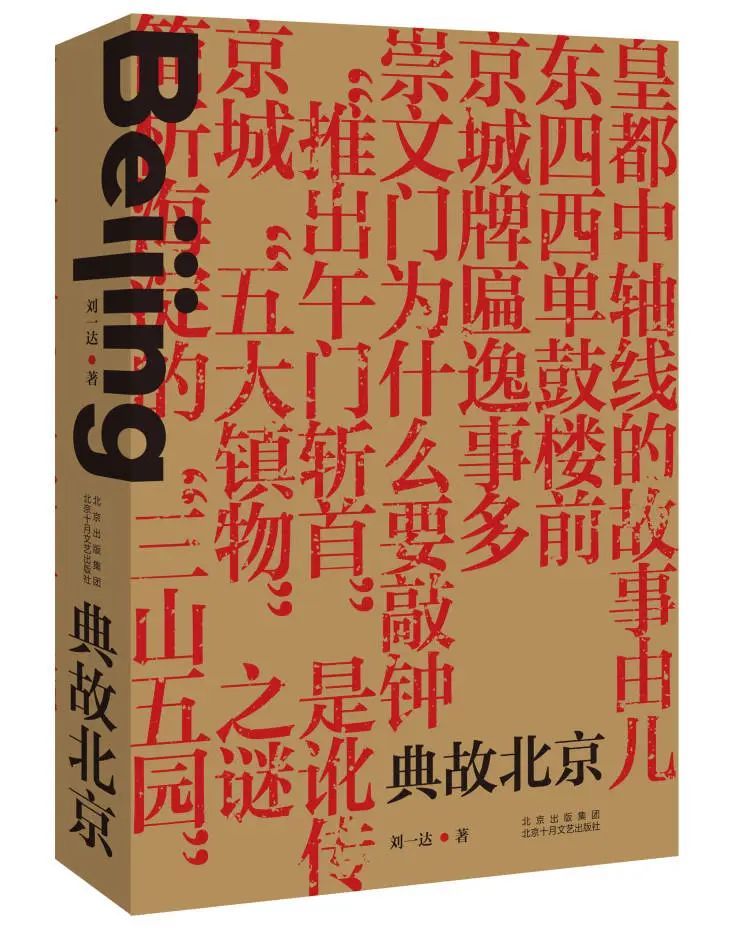
《典故北京》,刘一达著,十月文艺出版社,2020年11月
《典故北京》
刘一达
记得两年前,跟两个外地朋友逛新修的前门大街,修整后的前门大街通了有轨电车。
这是北京最早的电车,因为最初的电车上装着铃铛,开起来铃铛“当当”直响,所以老北京又把这车叫“diɑngdiɑng”车,有音没字,只能写成“铛铛”或“当当”车了。
当然,现在的“diɑngdiɑng”车只是一个观光项目,并不是北京人出行的代步工具了。看着“diɑngdiɑng”车的轨道,我对那两个朋友感慨道:“你们知道脚下踩的是什么地方吗?”
“什么地方?这不是有轨车道吗?”一个朋友笑了笑道。
我对他说:“没错儿,是有轨车道。但你们知道吗?这条道是老北京的中轴线呀!”
“中轴线?”
“对呀!你们往南看,这条线一直到永定门,往北看,这条线一直穿过正阳门,也就是前门,穿过毛主席纪念堂、天安门广场、天安门,穿过端午门故宫的三大殿,穿过神武门,穿过景山、地安门,一直到鼓楼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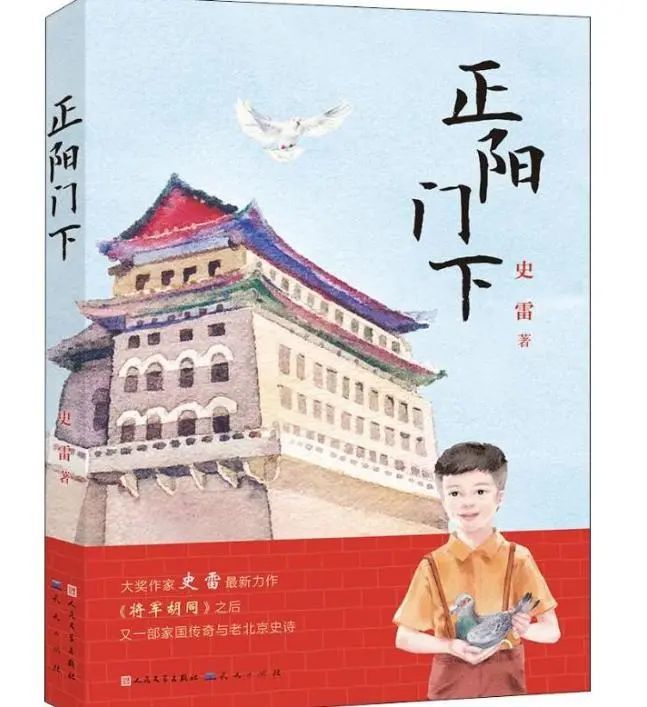
《正阳门下》,史雷著, 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8年8月
《正阳门下》
史雷
我在白骆驼上高高地举着标语,那上面写着“和平”两个大字。
白骆驼走得不紧不慢,终于过了中华门,前面就是正阳门了。
旦子仰头问我:“看到你二舅和大宝了吗?”
“没有,人太多。”我回答说。
“别着急!”旦子安慰着我,“马上就到正阳门了。”旦子的话音刚落,正阳门的方向就传来了坦克履带碾压路面的“轰隆”声,然后就是锣鼓声、欢呼声、歌声和掌声。
“怎么了?”旦子一边走,一边仰着头问我。
“是坦克的声音,可是怎么没有尘土呢?”我朝南望去。
“一大早,大家就往路上泼了水,尘土起不来了。”一个维持秩序的人笑着说。
编校:曾子芙;审核:丁鹏;核发:霍俊明配资优秀炒股配资门户
Powered by 配资平台鑫东财配资_期货鑫东财配资十倍_新股鑫东财配资 @2013-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